黑色“小偷家族”|河南父亲出租五孩子给盗窃团伙,一子疑被虐待致死
文|王一然 编辑|王珊珊
14岁的刘富兴有过三四个干妈。她们给他买衣服,带他去剪头发,洗澡,把他打扮得像“大高楼里的小孩”。白天,干妈带他在城市里走,“卖衣服、卖玩具的地方,很多大高楼,有电梯”,他不用做任何事,只是跟着干妈走,有时是跑。
刘富兴有时会被警察带去派出所,“是你亲妈吗?”警察盘问。刘富兴一言不发,被领出去后,就会换一个干妈带他。刘富兴说,他在外面没挨过打,只是要不停换地方睡觉。
两岁时,刘富兴就被父亲租给盗窃团伙,六岁快要上学时,才被干妈送回来。没过多久,父亲就开始打他,用烟头碾在他的手背上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他的手脚都被捆上,嗓子哭哑了,母亲被父亲一脚踹在地上,吓得发病,抱着捡来的玩具熊,当自己的孩子哄。
刘富兴有七个弟妹,其中五个都被租出去,弟弟跟着去偷超市、妹妹租给卖黄碟的打掩护。在刘家孩子不多的记忆里,他们一直在很远的地方奔走,那些地方坐很久的火车才能到达,一直走,在人群和商场里穿梭迂回,一直走,身边的大人不停更换,一直走,直到最后回到家,走就变成了跑。
六七年来,刘富兴陆续带着家里的几个弟妹逃跑。他们白天在街上四处游荡,晚上睡在街边、桥洞和废弃房屋里,如果被父亲抓回去,等待他们的,是新一轮的毒打。
无休止的逃跑被一段视频终止。今年8月,河南省商城县双椿铺镇赵畈村村民刘明举将老六捆在床板上,被邻居发现报警,并将孩子被捆绑的视频发在网上;9月6日,当地法院判决撤销刘明举和妻子为6个子女的监护人资格,刘富兴被送入中学,弟妹们进了福利院。
一位记者告诉刘富兴,曝光后,其他孩子就能避免像你们一样出去受苦。刘富兴愣了愣,看着他。
对刘家孩子来说,身处异乡颠沛流离的那段隐秘时光,才是日子里少有的糖:他们曾在寒夜里彼此分享外面的世界,甚至寄希望于“干妈”。“老三想回去。”刘富兴把头偏过去,“他干妈对他好着咧。外面好……回来干啥?回来就开始挨打。”

(已经被福利院带走的孩子,从左至右依次:老八、老七、老六、老五、老三。石闯摄)
三蒯子家的勺
刘明举外号三蒯子(kuǎi),在双椿铺,这是“傻子”和“无赖”的意思。三蒯子的妻子李少菊得过小儿麻痹症,口齿不清,发病时抽羊癫疯,不认人。李少菊上了三次节育环,都被刘明举逼着取了下来。两人没领结婚证,一共生了八个孩子。
村镇里,没人知道刘家孩子的名字,他们全被叫做“刘勺小孩”“三蒯子家的勺”,“勺”和“蒯”一样,也是傻子、无赖的意思。三蒯子打起勺子可一点都不手软,打井的铁锨、手腕粗的棍棒、随手抄起的拖鞋,还有手指粗的麻绳。
刘明举打孩子,也打妻子。有次半夜,刘明举睡不着,起身踹醒妻子,用凳子砸她,刘富兴在床板上闭紧眼睛,手按着老三让他别乱动,孩子们一个按着一个装睡,直到父亲发泄完,再集体逃跑。
黑暗里,父亲的呼噜声一声比一声大,刘富兴仔细听着,弓起身子,像只随时准备攻击的小猫。他一点点向床外挪,趿拉着拖鞋,走到窗前,一点点将窗户打开,直到出口能容下一个十几岁孩子蜷身而过。他双手一撑,整个身体像只小燕儿,半跪在窗台上,回身冲弟弟轻声喊:“走!”
六七年前,弟妹们都在外地,家里只有刘富兴一人,没人帮他看着父亲是否醒来,离窗户还有一步之遥时,刘富兴总是心惊肉跳,怕回身撞到父亲狰狞的脸,像平常一样抓起他的头发,喊着“我打死你个小畜生!”现在,他有五个弟弟妹妹,逃跑团队开始壮大起来。
有时,刘富兴没有机会逃出去,就躲在杂物堆里,等父亲离开再跑,如果刘富兴跑了,老三与老六就变成了“重点捆绑对象”。解绳子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——无论是谁,只要解了绳子,就要挨刘明举的打,即使是刘明举的岳母、孩子们的姥姥高秀芬也不例外,高秀芬和老伴儿回忆,刘明举曾威胁他们,管闲事就拿雷管炸掉他们家。
孩子们几乎不怎么上学,因为父亲会在放学路上堵他们。

(老六被捆绑在床板上,两个最小的在旁边陪他,孩子们都光着身子。视频截图)
几个月前,刘明举又把老六捆在床板上,手脚腕的肉被绳子勒得微微凸起,邻居们怕刘明举闹起来,不敢解绳子,用手机拍下视频,又报了警。“警察敢解,我们不敢啊!”一位目击者说,派出所的警察来了之后,把老六放了下来,舀了一大瓢凉水,老六抓过来,大口大口吞咽,噎得要吐出来,说不出话。
刘明举被曝光后,许多爱心人士和媒体涌入了刘家。“捆小孩是怕他出去害人,偷东西。”刘明举说,几个孩子在外面出租时,学会了盗窃和开锁。但据其他村民说,刘家的孩子只是调皮,有时候会破坏东西,但没听说偷过东西。
最终,刘明举与李少菊被剥夺监护权,老大被交给学校监护人,其他孩子都被带到商城县福利院。
“我损失了不少钱!”刘明举牙齿黄黑,额头上有个硕大的包,一双三角眼总是斜着看人,他是村里的贫困户,几个孩子也都有低保,今年开始,每个孩子涨到了每月252元,钱都打在刘明举的账户里。
事发后,刘明举跟在村干部后面,“不把小孩带回来我就喝药!”负责扶贫的村干部说,刘明举把农药瓶子倒在鱼塘里,嘴上泯了一点,被送到医院抢救,“回来后发现鱼死了,又管村里要钱。”
在刘明举眼中,孩子总是和钱挂钩。出租孩子时,租金一度从500块钱每年涨到了4000块钱;领低保时,孩子的钱也都进了自己的口袋;很多爱心人士捐的钱和东西,也都被他收了起来,曾有人给刘富兴一部黄色的老人机,被刘明举抢了过来自己用。
按照村民的说法,也有人怀疑刘明举虐待孩子是因为精神有问题,前段时间,他被送到精神病院去,他在里面打牌,大吃大喝,没多久又给送回来了。回来后他到处说:“里面有吃有喝,下次送我还去!”
刘明举有一条黄色的土狗,叫翘嘴,跟了他17年,形影不离,“狗听话得很。都要听话,小孩女子不听话不得打呀?”刘明举一脚将狗踹出去,翘嘴翻了个趔趄,又回到刘明举脚边缩着,过了一会儿开始摇尾巴。

(刘明举,村里人称他“三蒯子”。王一然摄)
冬夜里飘着彩色小马
村里没有孩子相信刘富兴说的话。草莓牛奶、黑色的鸡蛋和杯口粗的火腿肠,刘富兴每次说吃过,都惹来其他孩子的嘲笑,“刘勺小孩又撒谎啦!”
但刘富兴记得那些食物的味道。黑色的鸡蛋,吃着有肉味儿;桶装的方便面,里面有小块的肉丁,含在嘴里很久都舍不得吃掉。刘富兴说,他被干妈带着坐火车,去很远很远的地方,一路上买了很多好吃的。
老三刘富贵的经历和刘富兴差不多,到了出租老三时,刘明举每年能有一千多的收入,老三告诉刘富兴,他在外面“抓超市”,专门在一些大超市帮干妈偷东西;到了老五,已经有三千块钱左右。“租孩子的女的说,是带小孩卖黄色光盘,被抓到了,孩子一哭就放了。”刘明举说。
老五和干妈被警察抓住了。刘明举回忆,警察盘问时,“小妮儿说是她亲妈,警察带着做亲子鉴定,一看不是。”刘明举被警方通知去上海接老五。
据村民们描述,近几年,带老三出去的干妈回到了附近乡镇,开了连锁超市,不再做租孩子的生意。
今年正月,老六被送回家,完全不接受刚见面的父母,“你们不是我爹娘!”老六想跑,被刘明举掐着脖子拉回来,一脚踢在胸口,“跑了你狗日的!”
刘富兴看见弟弟挨打,撒腿就跑。他已经摸透了父亲的脾性,只要一有新孩子回家,被打的最狠的就是他,“不知道为啥,总是先打我。”刘富兴记得,老三回来时,他被父亲扔进粪沟里。
回家的孩子很快就掌握了逃命的窍门:跟着哥哥跑。老三刘富贵很听大哥的话,老四跑得慢,很多次都只能留在家里挨打。老五和老六性格孤僻,管母亲喊“勺妹儿”,喊父亲“刘勺”,笑话大哥刘富兴是“勺娃”。
“他们就不是吗?”刘富兴躲起来生闷气,老三找到他,给他半个烂苹果,“才在垃圾堆翻的,大哥吃吧。”
老三敬重大哥,但对弟弟妹妹暴戾,“富贵拿棍子敲他们头。”刘富兴比划了一下,“像俺爸那样。”老五和老六因此很听他的话,叫老三“大哥”。
村民何国富对刘明举家的孩子有印象,是几年前一个入秋夜晚。何国富打牌回来,看见灯下有两个箱子在动。
他第一反应是“谁家的小狗拖箱子耍”,路过一瞥,其中一个黑脑袋瓜冒出来,何国富吓了一跳,是两个小男孩,头发粘在一起,在灯光下泛着焦黄,脸脏兮兮的。
后来何国富才知道,他们是刘明举家的男孩,白天四处游荡,晚上几乎都睡街上。

(孩子们街上的“常驻点”,除了冬天,他们晚上几乎都睡在摄像头的灯下。王一然摄)
孩子们最常睡的地方,是三里坪镇的主干街上,一个电线杆子旁,那里有盏瓦数很高的大灯,夜里照着像炉火一样暖和。夏天时,这里是蚊虫聚集地,孩子们无法睡觉,刘富兴就带着大家围着电线杆子闭着眼睛走,免得被蚊子咬。
冬夜里,他们躲在一处没盖好的小楼顶层,就在老三干妈开的超市不远处,老四吵着冷,刘富兴和老三刘富贵把他围起来,凑在一起取暖。
“以后哥带你吃棉花糖。”刘富兴说,干妈曾买过棉花糖给他吃,到嘴里就不见了,甜得很。
“我也吃过!”老三说,“我还吃过牛肉串!这大!”刘富贵比划出一个夸张的形状, “俺干妈买的!”
刘富兴拽了拽他:“你干妈还给你买啥?”
刘富贵告诉大家,干妈带他去过一个很大很大的游乐场,里面有彩色的小马,飘在空中,小孩可以骑在上面,“还有滑梯,知道不,是一个很长的桶子,小孩一下子滑下来好久,从地下钻出来。”
刘富兴不说话了,他没去过游乐场,更没骑过那样神奇的小马,让老三讲了好几遍听。
第二天,刘富兴带着弟弟们去超市,希望三弟的干妈能收留他们,带他们去有游乐场的地方。超市的老板娘给了他们一些零食打发他们走,“你们太大了。”老板娘对刘富兴说。
刘富兴安慰弟弟:“长大就能跑的更远,能去坐火车,就能去游乐场了。”
即使是在街上睡觉时,孩子们也分配好职责,一个人醒着放哨,其他人睡;等醒着的人困得不行,再叫醒下一个,以防被父亲抓回去。
有一次刘富兴带着老三在街上,靠着一个小楼梯休息,见到父亲摇晃着走来,刘富兴掉头就跑,快跑到别的村时,他停下来,大口喘着粗气,发现老三并没跟上。他放心不下,跑回去查看,结果被刘明举抓了个正着。
刘富兴回忆,那一次,父亲用铁锨戳他的胳膊,至今还在靠近手腕的地方留下青黑的疤痕,看着大哥挨打,老三在旁边偷偷哭。那次被抓回去后,刘富兴就在街上找了几个不容易被发现的藏身点,遇到危急情况,他负责引开父亲,其他孩子就藏到藏身点去。
在刘富兴的心里,某种意义上,母亲是父亲的帮凶。“俺妈说我们偷东西,弄坏东西,其实都是她弄的。”父亲经常听信母亲的话,把他们吊起来审问。不管他们承认还是不承认,都会遭到虐打。
被租出去的几个孩子,回来后都与母亲李少菊很少亲近。母子间少有的温情记忆,是一次老六被刘明举反捆在床上,李少菊在一旁发抖,不敢说话,刘明举踹了老六几脚,就出门了。老六盯着李少菊的眼睛忽然喊:“妈!救我!”
李少菊用力站起来,歪歪斜斜朝老六走过去。
“他叫我‘妈’,我高兴,不怕打。”李少菊说,她的手使不上劲儿,很久才解开老六的手脚,老六几乎没有缓身,蹭着床板站起来转头就跑,留下母亲守着空空的绳子。
刘明举回来后,用拳头狠狠捶了李少菊的胸口。

(刘家门口的鱼塘,刘富兴说他们曾被父亲逼着喝鱼塘的水。王一然摄)
弟弟长出青草
两年前的秋天,天已经有些凉,刘富兴记得,老四刘富有光着脚晚上会冻得发痒。有一天,刘明举说丢了钱,拿出铁锨要打他们,刘富兴拽起老三就跑,但老三被父亲拽了回去,老四刘富有也没敢跟着跑。
刘富兴在街上躲藏了三天多,直到老三来藏身点找他,眼睛直勾勾的,像被吓坏了,“富有被开水给烫了,肉都掉没了。”
刘富兴回家时,老四刘富有已经认不出来原来的面貌。从头到脚,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,肉皮一碰就掉落下来,不停往外冒着血水,疼得腰直不起来,缩在地上。
老三告诉大哥,“刘勺捆的,妈烧水烫的。正面背面,都浇了开水。”
据村干部回忆,当时,刘明举带着老四到镇上医院,镇里建议马上转县医院,刘明举说没钱坐车看病,带着孩子管村里要钱,村支书往刘明举的卡里打了五千块钱,但刘明举没带孩子去医治。
村干部说,见到老四刘富有时,他背驼得厉害,疼得缩成一团,只能被刘明举提着走,大家说“孩子都直不起身”,刘明举笑笑说“不打紧”,一只手掐住老四的脖子,一只脚踩住他的脚,用力一抻, “抻抻就直了。”刘富有的身子剧烈颤抖。
刘富有的尸体是在水沟里发现的,在烫伤的五天后。关于刘富有的死亡,村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:据刘明举说,他回到家用酒精给老四擦身体,伤快好了,结果掉在水沟里爬不上来,饿死了;而刘明举的岳母说,孩子烫伤严重,还被刘明举用脚踩过,快活不成了,被刘明举扔在水沟里。母亲李少菊描述,刘明举逼着她烧开水,把孩子捆起来烫,“他说我不烫孩子他就要烫我。”
老四刘富有就埋在刘明举家后面的地里,刘家几乎每天都能见到那堆没有墓碑的小土包。
“富有死了。”刘富兴说。
“啥是死了?”老三问。
“就是永远都见不到了。”
“那我想和富有玩呢?”
“不行,他被埋土里了。”刘富兴甩开老三,一个人跑到鱼塘。
“要是那天我把老四拉跑了就没事了。”刘富兴垂下头,咬着嘴唇。老四死了很久之后,他靠近过一次老四的坟,那里和平常的荒地没什么不同,长满了摇摇晃晃的野草。
“看他干啥?我给他烧纸钱纸钱都不飘,没良心。”刘明举说,他每年都给儿子烧纸,并称孩子是被姥姥姥爷烫的,与自己无关。
弟弟死后,刘富兴几乎不再回家。他五官秀气,有高高的鼻梁,眼神比鱼塘的水还澄澈,即使脸上身上都是土,还是有村民愿意给他剩饭剩菜吃。
一旦刘明举知道谁给孩子饭吃,就找上门去。“我家小孩吃了你的饭肚子疼!”刘明举赖在门口不走,拽着刘富兴的头发过来,“拿钱给小孩看病吧!”长此以往,不再有人愿意接济孩子们,其他孩子也不和他们说话,他们只能在垃圾堆里找食物。
刘富兴的小学同学小凤说,在少有的上学日子里,学校的同学都嫌弃他,喊他“刘勺”,“五年级的时候还在班里拉尿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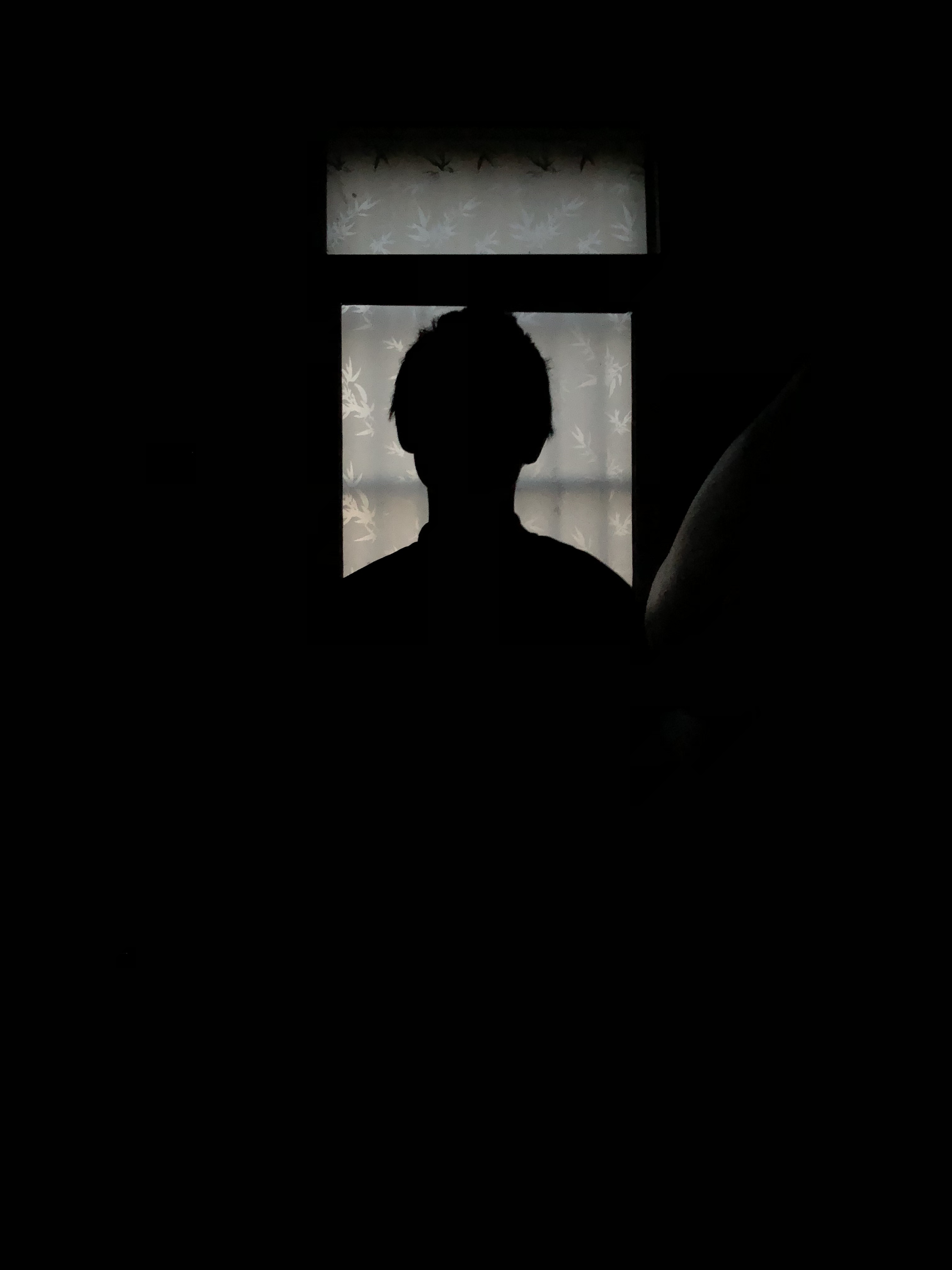
(刘富兴站在姥姥家仓房窗前。王一然摄)
就像抱儿子那样
刘明举捆绑虐待孩子的视频曝光后,除了刘富兴,其他的孩子都送到了福利院。刘富兴已经快15岁,政府在新学校给他找了一名九年级的班主任,做他的学校监护人。“不能让他爸有任何机会抓走他。”监护人许老师说,刘富兴上了六年级,平时住校,周六日回姥姥家,老师护送回家,姥爷再送去上学。
刘富兴喜欢听同学大声叫:“刘富兴!”不知道名字的,也会叫他“刘娃”,没人再叫他“刘勺”。很多同学都看过他弟弟的视频,知道他家里的事情,帮他写没完成的作业。
但还是少有同学愿意和他做朋友,宿舍是通铺,谁也不愿意和刘富兴挨在一起,“离我远点,你臭!”刘富兴被挤到一边,老师只能安排他单独睡一个床铺。
监护人老师说,刘富兴总是畏畏缩缩的,一双眼睛老盯着学校的摄像头看;送刘富兴回家时,老师问:“你在食堂吃得饱吗?”刘富兴“嗖”地躲在姥姥身后,探出头来说:“吃不饱。”老师拉过他,他眼睛眨了几下,“只敢吃一勺饭,怕他们说我吃得多。”
刘富兴身上穿着黑色的宽大夹克,下身是紧身牛仔裤,一双略大的白蓝色运动鞋套在脚上,鞋带还是新鞋的样子。这是老师给他新添的行头,刘富兴把手缩在宽大的袖子里,一直左右张望,自从弟弟妹妹被抱走后,刘富兴没了跟班,总觉得害怕。
母亲李少菊并不怎么搭理大儿子刘富兴。她梳着短发,穿一件黑红花袄,眼神呆滞,倚在门口,怀里整天放着老八的照片,老七和老八都在她身边长大,没被租出去过,跟她格外亲。李少菊去福利院时,不到两岁的老八拽着她不撒手,哭了起来,李少菊也跟着哭。
镇上的村民说,出事后,刘明举到镇上炫耀“曝光了还挺好,我每个月多2000块钱”,没有人主动和刘明举说话,他们私下里转发刘明举的视频,见了刘明举就走开。

(刘明举夫妇与老七老八合影,除了幼年就被拐走的老二,只有这两个孩子没有被出租过。王一然摄)
入秋之后,小镇气温陡然下降,枯叶开始掉落,地里烧起麦秸,冒出清冷的烟。刘富兴趿拉着母亲的拖鞋走出来,后脚跟悬在外面,不时活动冰凉的脚趾。他把老师买的新鞋每一处都细细刷过,“同学嫌我臭,洗了就好了。”
刘富兴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弟弟妹妹们了。家里8个孩子,老二丢了,老三暴躁,老四死了,老五老六孤僻,剩下两个小的还不懂事。他没有朋友,总是在课堂上发呆,想着和弟妹们一起的日子。他不确定还想不想回到那个家里,也从来没恨过谁,“大家都讨厌我,我不能再恨别人,没资格讨厌他们。”
弟弟刘富有死后,父亲的脾气变得更大。有一次,父亲发火,说家里的东西被刘富兴搞坏了,跑到灶台边抄了一把菜刀,“他要杀了我……”刘富兴的声音有些颤抖,以前,父亲也说过这样的话,他没当回事,认为“长大了就能跑远了”,但亲眼见到老四被埋起来后,他觉得后背发凉,拼命挣脱了逃跑,“他真能杀了我!”
可刘富兴没有像老三和老六对父亲憎恨,一心想回干妈那儿去。几个孩子中,只有他还叫“爸”“妈”。他有一个秘密,连最亲近的老三也不知道——他笃信自己被租出去前被父亲抱过,别的孩子都没有,“就像抱儿子那样。”
(文中刘富贵、刘富兴、刘富有、高秀芬、何国富为化名)
